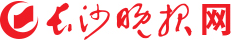散文 | 多面天心
■沐刃
来长沙二十多年了,与天心的交集其实相对偏少——因为,我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基本上在芙蓉、开福一带。
1996年,以前的“南区”改名天心区,其命名来由无疑与天心阁有关。能够以一地的名胜来为区划命名,延续一座历史名城的文化根脉,连通历史与当下,构筑起共同的记忆与认同,这当然是幸事,更是一桩美事。
作为长沙仅存古城标志之一的天心阁,声名自然响亮,可我与它的第一次接触,却已是来长之后的第七年——难道真如有人所说:对于身边熟悉之地,我们往往以为能轻易抵达或拥有,便不知不觉间怠慢了?
那时老婆正有孕在身,短短几天的春节假期,回老家团聚难免奔波折腾,于是邀请父母来长过年。正月初一,我们阖家出游,选择的目标就是天心阁。
进公园大门后,徐徐前行,抚摸着古城墙上的窑砖,我们发现,似乎每一块墙砖上都刻有匠人名号,这做法彰显的是一种严苛的责任与溯源吧。
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还有崇烈亭、崇烈门与崇烈塔。它们都是大有来历的,就是抗战胜利后专为纪念长沙会战中阵亡的将士所建。崇烈门上的两副对联——“气吞胡羯,勇卫山河”“犯难而忘其死,所欲有甚於生”,字里行间,透露出不容轻视的坚毅与民族气节。
后来,去天心阁的机会就更多了。有一两年,儿子在旁近一小区学习吉他。每次送他到老师家之后,我就独自到天心阁溜达。有一次,太阳刚刚升起,阳光斜穿过树叶,在地面洒下斑驳的光影,我蹲下身子,在一条僻静的小径上,观察一群蚂蚁忙碌却井然有序地搬运着游客遗落的面包屑,它们那种目标专一的简单,我最为羡慕。
莎士比亚曾说,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同一片土地,不同的人所钟情的面向,各有偏好——南城天心令我欢喜的,除了天心阁之类名胜古迹所代表的传统及人文的一面,还有它的动静皆宜。
先说说动吧。位于回龙山下西侧的白沙古井,经年流淌、不溢不枯,取水者来来往往,井沿上百态众生……清冽的泉水无声流淌间,时已移,世已变。或许,只有它算得上真正的阅人无数吧。
贺龙体育馆和解放西路酒吧一条街,则分别演绎着别样的动感。虽然酒吧一条街的喧闹与躁动,于我是极不习惯的,但是,也曾陪外地来长客人体验过三两次,见识了一座城市夜生活的诱惑与性情。
天心的静,在我看来,首先体现在点缀其间的老街巷:坡子街、化龙池、大古道巷、太平街、下河街……其实,如今信步在这些街巷,应该说没有多少纯粹的老与旧了——老是有一点,新也有一点;古朴摸得到,时尚闻得着。也许,这杂糅与并存,一切自有其内在逻辑,真实的世态也不过如此吧。
在南城天心闹中取静另一个好去处,便是简牍博物馆。目光聚焦于一片片竹简,那一枚枚略扁而修长飘逸的隶体文字,总让人忘记时间的流动。每当在那样的场景,我总在想,不要低估了当年那些平凡而琐碎的书写,一旦穿越时空,传之后世,便成为一种鲜活的证据,传递着事关政务、赋税、民生、风俗等极为丰富的信息;我也禁不住从内心钦敬那些竹简整理者,工作枯燥、甘受孤独,却从未放弃对竹简上文字的追问与解读。
一直以为,城市濒水而起,因市而兴,因人而盛,但真正令其声名鹊起的,往往仰仗于为数不多的名人大V,以他们的文字与事功,他们与城市的交集与轶事,譬如孔子之于曲阜,柳宗元之于柳州。大唐之时的杜甫结缘长沙,就在天心。诗圣晚年两度驻足长沙,曾寄居江阁,在长沙留下诗作五十余首。
2005年开放的杜甫江阁是原址重建的,我从未登临,却喜欢立于对面的橘子洲头隔江相望,因为我认为,这江阁,是适宜于仰望和想象的。
位于太平街上的贾谊故居,有一次专程去拜访,好像是2014年底吧,没料想恰好遇到闭馆维修,不免有点失望。也好,这念想一直留着,便也是一种期盼与动力。
当然,这片地域上值得探访之人,还有药王孙思邈、书法家何绍基、伟人毛润之等,以及因人而名的药王街、第一师范,火宫殿、臭豆腐……
在我看来,天心确实是一块多面体,总有一些美好能把你打动。至于魅力如何,当然要靠你自己去体验了。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