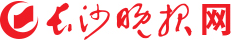散文 | 清凉之境
晓寒
夏天来到小城后,窗外的阳光一天比一天黏稠,堆满了街道和高低错落的屋顶。望不断的空中,伴着隐隐约约的蝉声,似有谁的手在一把接一把地撒着金花,刺得人眼睛酸痛。屋子里大大小小的家什,都冒出一股灼人的热气,原本清凉的处所,渐渐变成一个蒸笼。
屋里装了空调,事实上它们更像一种摆设,因为我很少打开,那看起来温情脉脉的钢铁,总会在不经意间弄伤我一根骨头、一个关节,在我身体里留下一处又一处暗伤。当初之所以买回来,似乎是一种心灵的需要,仿佛有它的存在,便能震慑酷暑的兴风作浪。
很多时候,我们花钱买到的只是一种安慰,我们乐意活在这种亦真亦假的安慰里。现实是,不管有多少消暑设备的存在,酷暑从来就没想到要放过我,它时常把我弄得心烦意乱。我和它斗过多个回合,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我自知不是它的对手,最后只好采取迂回战略,和它握手言和。
酷热难耐之际,我会躲进书房,坐在那把老式木椅上,把音响打开,听几首熟悉的老歌,那些歌都是我平常听惯了的,像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凤飞飞的《月朦胧鸟朦胧》、邓丽君的《在水一方》之类。我生来就是个怀旧的人,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那些旧时光里。我承认我是个没出息的人,从未想过要挣脱那些陈旧的时光,去搏击明天的风雨,追逐那些别人念兹在兹梦寐以求的东西。随着歌声流水般响起,眼前的画面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一回放。
最先出现的是我午夜梦回的乡下中学,那里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北风台。老式的红砖房子,草绿色的玻璃窗,三面被田野拢着,右边有一道河湾,河水清澈,蒹葭如岸。每到傍晚,教几何的李老师会领着我们去河湾里游泳,水花飞溅,笑声四起,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波光粼粼的日子。接着来到眼前的是我的老屋,泥巴墙,瓦屋顶,嵌在半山腰。门口一排排的梯田,黄色的稻子一起一伏,像一架庞大的梯子,架在层层叠叠的群山之中。午后,我躺在一张竹床上,鸟鸣婉转,山风徐来,不一会就酣然入梦。待我醒来,外面云淡天阔,阳光挂在门前的雪梨树上,屋边那片幽深的油桐林里,传来几只蝉长长的嘶鸣。
歌声在不停地流转,屋子里突然变得清凉起来,仿佛那歌声带来了习习清风。
有时候,我会泡一杯绿茶,芽尖儿在水里缓缓打开,让我想起乡间那些采茶的日子,沿着田埂,踩过木桥,听着断断续续的溪水,走进细雨蒙蒙的春天。把茶放好,然后坐下来,从书柜里随手抽一本书,抽到哪本就是哪本,可能是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也可能是川端康成的《雪国》,还可能是山多尔的《烛烬》,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撒旦探戈》。夏天不是读书的好季节,读书的目的被彻底淡化,在乎的是那样一种形式、一种仪式感。拿在手里随便翻,翻到哪页就是哪页。
“在施伦茨,圣诞节那天,你从酒馆里望出去,白雪明晃晃的,真要刺伤你的眼睛,你看到大家从教堂往家里走。”“山沟天黑得早,黄昏已经冷冷瑟瑟地降临了。暮色苍茫,从那还在夕晖晚照下覆盖着皑皑白雪的远方群山那边,悄悄地迅速迫近了。”海明威和川端康成的雪,有着同样的质地,轻轻的,淡淡的,不着痕迹地带来瑟瑟寒意。推开山多尔笔下那座庄园的大门,瞬间就被一种灰蒙蒙的古老的气息包围,看到的是摇曳的灯光,望不到尽头的群山,黑夜来临,各种兽在群山之中对着庄园嗷叫。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那场雨,巨大、绵密,无休无止,笼罩着原野和山川,充满了毁灭的力量,又带着比黑夜更加漫长的乌托邦式的希望。
茶叶在杯子里漂漂浮浮,歌声把整间屋子填满。在歌声和书与茶里,酷热似乎慢慢退去,渐渐进入一种清凉之境。仿佛听到窗外草虫在低低地吟奏,落叶窸窸窣窣地响着,桂花凋谢,菊花开了,大雁带着忧伤的叫声,正从头顶飞过……
这些年的夏天,我几乎都是这样度过,我也渐渐从中明白,酷热并非不可战胜,最难战胜的是我们的内心,它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