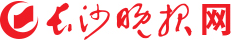罗瑞花:乡村三月
灿烂春阳里,我回到了青溪的木屋,母亲领我去看她的菜园。
站在竹篱边上,满园的蔬菜竟然盛开着繁花。冬白菜早已开始演绎春的缤纷,菜薹长出了茎,嫩绿的叶间开着金色的花,黄绿相应,赏心悦目;香香的芫荽不再匍匐在地,而是向上生长,开满了细小奶白的花;白胖胖的萝卜一半露出土面,茎上绿叶间的白花在风中摇曳;特别优雅的是那一畦娇嫩的葱,圆茎上顶着淡紫色的球状花序,可爱极了。
我随着母亲来到园子最里端,篱笆下有一小块葵菜,叶圆如猪耳,颜色正绿。边上几株留种的葵,高大繁茂,满枝的叶子中间也开出了细小淡紫的花。
母亲说,菜都老了,开花了,摘些葵叶做汤菜吧。
在蜂飞蝶舞的繁花中,摘着嫩滑的葵叶,我真切地感受到,美好的日常都是艺术。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哥哥姐姐都去学校读书了,母亲去生产队出工,留下我一个人在家看屋。我做好母亲吩咐的小家务,就坐在门槛上眼巴巴地盼着母亲收工回来,母亲总能给我带来惊喜:油桐叶裹着红红甜甜的三月莓,粽粑叶包着酸酸的山杨梅;柔韧的葛藤拴着白白胖胖的葛根;蓝印花的手帕鼓鼓囊囊,打开一看,是朱红的山栗;金黄的斗笠装满粉红的米浆菇;雪白的搪瓷茶杯里躺着三五个淡蓝的鸟蛋……
这些,在母亲,那只是青山绿水中的一随手,而在我,那红绿、红白、蓝白的搭配以及粗笨用具中灵动的生命,不仅解了我的嘴馋,而且滋养了我的内心,给了我最朴素的美的启示,大自然物产丰盈,五彩缤纷,美丽如画。
母亲住的木屋五十年了,瓦片间长出了瓦松,屋檐鸟嘴一样翘起,雕花的窗格透进温暖的阳光,木门上的木栓光滑灵活,房屋四周的滴水沟用条石砌得整齐,檐间麻雀搭的巢,梁上燕子垒的窝,墙角蜘蛛挂的网……处处是生活。
母亲不习惯用秤称东西,总是相信她的米升子。煮饭蒸酒舂糍粑,收豆点麦种玉米,都是用米升子来衡量。平时煮半升米,鸡、鸭、人管饱,来了客人煮一升或者两升米;一斗(10升)糯米用多少酒曲,两斗糯米能舂多少个糍粑;腊八节煮几升豆豉;春节炒几斗瓜子花生……升子不仅是一个量具,更是日常的幸福。当母亲拿起升子时,不同时节不同的香味就会在木屋蔓延开来,一个个日子便有了滋味。竹制的米升子被时光染成了暗红色,被母亲摸得光滑油亮,分开刻着的“公平交易”四个字清晰可见。升子摆在那里,有准则,有温度。
母亲种茶,摘茶,制茶,卖茶,但不会品茶,连茶杯也没有。她所拥有的就是一只陶制的茶壶和一个陶钵。早晨起来,舀来井水,烧开,倒进茶壶,抓一把茶叶泡上,干活回来,渴了,倒上一陶钵凉茶,喝个痛快。这把褐色的茶壶腆着肚子,长着一个小巧好看的嘴巴,配上扎着圆形发髻的盖和弓形的提把,就像一个皮肤黝黑、饱经风霜的小矮人。它一直摆在灶屋的桌上,浸泡着茶叶,滋润着岁月。
糯米饭在石臼里舂成泥,一团一团地捏圆了,装进雕刻精美的模子,按紧,印上花纹,拿出来放在竹簟上,用劈成四瓣的筷子点上红印,晾干后,糍粑上的花纹凹凸有致,红印鲜艳惹眼。无须架在木炭火上烤,只要摆在你眼前,喜庆软糯的糍粑就把年节衬得富足、韵味。
在团箕里团得溜溜圆的元宵,用绿色箬叶包裹的粽子,柴火灶里酝酿的甜酒,彪形汉子肩上挑起的谷箩,手中舞动的彩龙,嘴里吹响的唢呐,巧手女子剪刀下的窗花,针线里的蝴蝶……
蔬菜,长着长着盛放出繁花;器物,用着用着显出了厚重;日子,过着过着便成了诗的章节。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