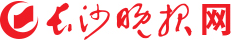散文丨“半边街”的记忆
■杨松林
七十年代的乡村有多冷呢?
现在坐在空调房里看着窗外夏天的我当然是感受不到了。如今在现代化教学大楼里读书的孩子们也是想象不到的,毕竟他们不知道,那时的乡下不是所有的孩子在冬天都会有棉袄穿,有的一身单衣便也过冬了。碰上下雨天更是扛不住,屋子本就阴暗,北边墙缝里还能听到风“呜呜呜”地灌进来的声音,再加上雨滴,冷便立即呈现南方特色——深入骨髓。
那时,我在一所土砖瓦房的乡村学堂读小学一二年级,周围的社员管这所学校叫“半边街”。“半边街”地方小,不似现在可以敞开了在过道、在风雨跑道上玩耍,只消几分钟就能全身暖和。那年月,我们得另辟蹊径。
女孩不用说,围成一圈自有她们的办法。男孩子呢,眼神一对,立马就往老师食堂边的暗道里跑,将老木门栓紧了,再全挤在角落里——“一二三,嘿——哟!”“一二三,挤嘿!”于此反复,卯足劲儿,等大家全暖和了,才满足地长叹一声,“好香呢!”然后活动活动筋骨,满眼放光地等待着下一轮。这项集体狂欢般的运动,我们称之为“挤油渣儿”。挤一次就能兴奋好一阵子,凭着这份兴奋,等待中午开饭的时间也就容易过多了。
我家离“半边街”比较远,学校特许我们可以自己带中饭来吃。所以每天来往的泥巴路上,除了背着缝有红五星的绿布书包外,还有就是手上提着个装满饭的“洋瓷缸”了。食堂的黎大嗲总会提前给我们热好饭,上午课一完,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饭盒,彼此展示一番就是一阵狼吞虎咽。饭很好吃吗?不过是一堆红米饭,偶尔来点没油水的小菜,洋瓷缸里多是饭多菜少。要是谁的饭盒里能有个煎鸡蛋,那他在那一刻就会成为所有人的焦点,享受着考试第一名才会有的来自小伙伴们的羡慕。然后,他会夹出一点点分给同伴。
小学的时光总是被玩乐充满,不论在课间还是课堂上。下了课,我们丢沙包、跳房子……玩跳房子的玩具,有用几颗算盘子拿根细麻绳穿起来的,也有从塘沟边捡来的铁螺陀壳串起来做的,都是自个儿想办法。晴天,操坪里玩的人多了,黄色的烟尘便会弥漫,随着欢笑声此起彼伏。上课了,我们聚在土砖瓦房的教室里,听龙老师给我们故事,年轻漂亮的董老师教我们学数学,唐老师还组织我们开展“生字听写比赛”,我在一次比赛中拿了第二名,学校在集会上还给我发了一张大奖状呢。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老师是严格的也是温柔的,学习是需要勤奋刻苦的也是有趣的,“半边街”是老旧的也是温暖的。
现在当然是见不到“半边街”学校了,就如同1977年秋天我入读一年级时再也见不到李家祠堂一样。
当年母亲领着我走进这所高大的土砖瓦房学校时,我还懵懂着,满眼都是长廊和伞柱,斑驳老旧的木门窗,黑漆漆的木板挂在教室前面的墙壁上,以及五六间房子坐落眼前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会是几年前能让我抬头仰望的李家祠堂。
还记得初次的踏足是跟随大人来这里参加社员大会,各生产队所有的社员都聚集在这个大屋场中,石头祠门,一座高台,大队支书坐在台上作报告,声音洪亮得很。台下呢,便是脸都朝着台上的方向、规规矩矩的社员,看上去那样子听得蛮认真的。那时我不到4岁,个子矮小,抬头看不见那个支书长啥模样,便干脆东张西望,仰起头发现一片方形的天空,“这是什么?”我奇怪地问。
“天井”,母亲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天井”,很奇妙。不仅因为它既能容许晴天阳光探下身子,也能纳下雨天顺着檐沟流下的雨水,还因为它的矛盾——无边的天与有界的井。到底是天塞进了四四方方的“井”里,还是“井”幸运地捕捉到了一片天,小时的我一直没有想透,何况我还来不及想,天井便没了——祠堂被拆了。
好多的男男女女,一队队,来来回回,秩序井然,原以为沉重得不可移动的祠门和高大的伞柱,寥寥间便消失一空,再眨眼,一个高大的屋场便没了顶,满泥巴地都是碎瓦砾。我是着急的,“这么大这么好的房子,怎么把它拆掉呢?可以住好多好多人呢……”我想上去阻止,但没办法,“他们不会听我的。”
后来我知道了,它还是能“装”下好多好多人,因为它成了“半边街”学校。一批批孩子从这里启蒙,从这里毕业,从这里一步步走向村外。
如今,我执鞭三尺讲台,日耀层楼,玉兰飘香,眼前逐渐浮现的却是四十余年前“半边街”的土砖木窗,野草蔓蔓,还有石笔在石板上吱吱嘎嘎一笔一划的大字,田埂上三三两两的欢闹,以及凝聚过全校目光的那条鲜艳的红领巾,当时她的一角又是何等荣耀地翻飞于我的胸膛。
往事再省,岁月有情。夏去冬将来,今冬吹来的风里不再是刺骨的寒意,而是存于记忆深处的朴素的老师、淳朴的玩伴、有趣的游戏……这些一同拥挤着,将油渣香味儿挤出,化成一股无边的暖意,支撑着我从“半边街”的这一头走向另一头。而待我行至另一头时,或许我还能看见一个仰着头的少年。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