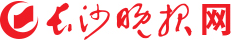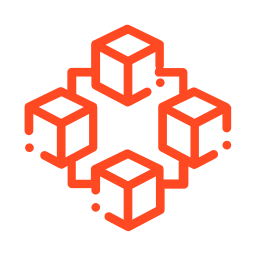父亲
苏君
(一)
父亲老了。
那天他站在梯子上,想把一桶水倒进水塔里冲洗内壁的沉淀,那一刻,地心引力仿佛一下子强大得不可战胜。他提水桶的手僵持着,慢慢地慢慢地,费了好些力气才把水桶送进去。这要在以前,那是多么轻松的举手之劳!
父亲老了。身体略微佝偻,面容变得松弛,头发大半斑白。最要命的是,两颗门牙掉了,张口笑的时候,牙齿的缺陷就暴露出来。而照片上年轻时的他,是多么阳光俊朗的一个小伙子,一笑就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
父亲中等身材,即使壮年的时候恐怕也不到一米七。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身材,却以力气大在我们当地著称。堂兄正强是个哇啦哇啦大嗓门的家伙,但在我父亲的面前却要声音低几度。“你爹是出猛力的人。”夏天乘凉时,他由衷佩服地说。父亲微微一笑,摇着蒲扇,回忆起了当年的战斗岁月。
那时候他在生产队劳动,收割稻子的时候他被安排运送谷子。同伴们恶作剧,把刚打下来的湿漉漉的谷子往两个箩筐里摇了又摇,压了又压,直到堆得满满的实在装不下才作罢。父亲在一旁拄着扁担呵呵地笑。等他们灌好了谷子,他一弯腰,挑起这担谷子上了田埂,大步流星一口气冲上了一里多远半山腰的晒谷坪。负责晒谷的裁缝七爹好奇地招呼他来过下秤。父亲刚把扁担挂上秤钩,只听“咔嚓”一声,栓秤杆的竹竿应声而裂,爆了。父亲说起这些的时候表情是平静的,他甚至谦虚地说起大伯父,挑一副担子走18里路不歇肩,那才是真正的力气大。
父亲确实是力气大。当他五十多岁的时候,我那时候三十出头。我们父子俩有时候嘻嘻哈哈“过招”,他轻轻一扒拉,我就到了一边去了。我从没占过上风。父亲的壮实也得到了村里人的认可,在一些需要出力的场合,像修路、送粮、伐木乃至老人过世出殡的队伍中,常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村里壮实的男人很多,包括叔叔伯伯在内都比父亲高大,为什么唯独对父亲的力量这么认可呢?
(二)
父亲在村里有很好的口碑,让他出名的不仅是力气大,而且干活麻利。他还有两手“绝活”。
“绝活”之一是栽秧。
在农村,栽秧就像学生写字一样,是一项基本功,几乎人人都会。可是父亲的本领是,他可以把一行秧无论多远,栽得像尺子量过的笔直!
之前我们那里为了把秧栽直,是有专门的农具的,叫“滚子”,那是一个呈“丁”字形的木制家伙。竖着的一端是把手,横着的一端等距离装上了碗口粗的轮子。栽秧前就扛着这个农具在田里拖过,那些轮子就会留下一道道痕迹。栽秧的人把秧栽在划出来的印子上就可以。后来嫌麻烦,大伙的做法就是挑一个会栽秧的,先在田的中轴线处栽一行笔直的秧,这个做法土话叫“开剖”,其他人以他为准一字排开在田里栽秧。每逢这个场合,父亲总被推选出来担任“开剖”的角色。
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我家分到了三亩多田。每次插秧,父亲总是领着我们先把田野中间的几丘小田收拾好,最后来收拾家门口附近大路边的一丘大田。
大田的一个角落围了几分田作秧田育秧。每次栽这丘田,父亲总是先带我和妹妹去扯秧,把秧苗拔出来洗去泥,再扎成一小把一小把的。估摸着足够他栽了,他则一手拎着一大捆秧优哉游哉先去栽了。
他先在大田的中央栽下笔直的一行,然后以这行为标准在两边继续栽,边栽还时不时地站直了左右看看。栽这丘田他是从不要求我们兄妹来帮忙的。等着这丘田全部栽完,从大路上过的人就会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无论站在路上的哪个位置看田里,看到的秧都是笔直的。这种笔直的效果一直到禾苗扬花吐穗,行距间的缝隙被消弭。父亲已经不仅仅是在栽秧了,他分明是在享受他的绝技展示----栽秧秀。
父亲把这一枯燥的农活上升为行为艺术,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的品位和追求是卓越的,即便是在农村领域以农民身份,也会不由自主的显露?
(三)
父亲的另外一个绝活是打砖胚。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建材逐渐走俏。机制砖大规模普及前,盖房子的砖是用手工打出来砖胚然后垒成窑烧制成的,俗称“窑砖”。父亲最擅长的就是打砖胚。很小的时候我就在他砖厂的工地玩,稍大一点就在他的工地上做小帮手,帮他把打出来的砖胚一块块放好。
父亲打砖胚打得又快又好,一团篮球大的胚泥在他手里几下就摔成模具截面大小,填模、切割、脱模一气呵成。有了我的协助,他的效率更高。一般每天可以打800到1000块砖胚。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父亲的力气很大——打1000块砖胚出来,如果用双模的话,相当于一天要在手里从早到晚揉搓、抛丢500团胚泥,没有点力气还真吃不消。
父亲打砖胚的动作像他栽秧一样很耐看:动作流畅,手脚麻利,随着重心的不停转换,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看上去简直就像是动作舒展的艺术体操,让人一看以为打砖胚是很容易的事。高二那年暑假我照例给父亲当助手,不过那次不是给别人打砖胚,而是给自家打。我曾经在看得心痒痒的情况下要求试一试,结果还没把胚泥举起来那泥就在半空散了,工作台上凌乱不堪,弄得我很是狼狈,最后乖乖地该干嘛去干嘛。
那个暑假父子俩忙活了一两个月,打了好几万块砖胚,全部烧成窑砖,最后盖了现在的这个房子。
打砖胚是个很耗体力的活,父亲却干这个工作干了二十多年。后来我们聊天聊起这个,他似乎也惊讶当年那么拼命,感叹道:那个时候连午觉都没睡呢!
(四)
年少轻狂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看不起父亲,认为他太平凡太普通。而现在,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觉得我越来越懂得了父亲,而且还在很多方面在自己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开朗、乐观,极易相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发脾气。我曾见过父亲和别人干架,有那么两三次吧。那时候父亲还很年轻,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每次干架的场合都是一大群人围着吵吵嚷嚷,只见父亲像一头豹子一样猛冲上去,一弯腰躲过对方的袭击,一把拦腰抱住对方,像扔面粉口袋一样横掼出去。
父亲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常常在我们念叨当年他的成绩是多么的好,由于家庭条件没能继续念下去是多么的遗憾。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几个俄语字母和短语的发音。
父亲只念了小学,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却始终保持对知识的敬畏。我一个堂兄是个铁匠,不识字,是个文盲。印象中以前有那么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吃过饭后他都会到我家来,请父亲帮他记工分。每次来,父亲总是很郑重地替他做这个事。我看过那个记工分的本子,工工整整的,依稀可以看出优等生的影子。
父亲在村里有个知交,夏四爹。四爹是个被划为地主成分的人,会古书,会书法,会乐器。村里人不知是爱好搭不上边还是恐惧走得太近怕惹祸,四爹在村里的朋友很少。父亲却不避讳这些,常到老爷子家串门,要么聊天,要么看他写字,要么跟他学拉二胡。有次赶集,他居然买了把二胡回来,于是,咿咿呀呀勉强成个调调的二胡声便在我们这个原本没有艺术氛围的屋子里扎根了。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