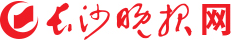散文 | 江南春
■董改正
朋友开茶室,取名“江南春”。
江南的春色,一篇相如赋也绘不全它的细部。草长莺飞,蝶飞蜂乱,繁花迷目,水色连天,一支最自由的笛也吹不彻江南的水面。这样热烈绚烂的春,与“人间正道是沧桑”一起,以铺张的修辞祝福着花红柳绿的人间。
2020年的春天是寂静的。已经几十天没有出门了,不知春色几许。道路两边的白玉兰紫玉兰,每年都是先于叶子来到人间的,像一只只鸟,细爪紧握着伶仃的枝丫,在料峭的春风里跌宕瞭望——不知今年如何?想象着井湖公园的樱花、湖水、芦芽和敏感的野鸭,回忆着去年春夜与好友觥筹交错的灯光和踏月同归的旧事,却只能困于斗室,肺腑间积满尘埃,胸腔内排满浊气,口舌上粘连不尽,渴望一次伐骨洗髓的涤净,渴望一杯今春的新茶。
亿万度春秋轮回的沧桑大地,依然会在悲悯的春风里醒来,引渡生命喂养生灵,予无数不安的心灵以温暖的抚慰。那一种名叫“茶”的植物,那一种立于“人”上,代祷苍天的灵性植物,它们苦涩的祷文唤来了慈悲的雨水。一尖尖绿光从干枯的枝上迸发,如翠,如歌唱的舌。那一点“尖”上,那一勾“舌”上,春光盈盈且嘹亮。它们携带着引导飞升的轻盈,在置换了人世的厚浊之后,还终将飞回它们辽远的故乡。
茶是苦的,原字为“荼”。所有背离“苦”的茶,都不该叫“茶”。茶是这个民族基因谱上的重要组成,茶里藏着它的文化性格,藏着它的审美密码。茶是或许无奈或许勇毅的承受,与对“原罪”的忏悔不同,它以“自讨苦吃”来自省,“苦中作乐”,然后“苦尽甘来”。茶里含着自觉的思考、自审、自我清洁和救赎。茶是释、是道,是中和,是消释。
那遥远的丝绸之路上,驼铃寂寞,帆影绰绰,运输的岂是仅仅作为饮料的茶?哪一方天空下哪一片土地上的生灵,不都是充满劳绩,却渴望诗意地存在,希望在每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引吭高歌?
开门七件事,茶居其一。茶很浅,浅到日常;茶又很深,深如遥夜。能够本能地天人合一,诗意地析出草木中悠远的意味,玩味,审美,并以仪式的方式进入日常生活的,也许只有我们这个民族吧。我们占卜的“易”,我们无邪的《诗》,我们定秩序的《礼》,甚至是用来救命的药典、药理、中医、中药,都带着看似玄妙的浪漫——阴阳?天人合一?
古人的茶,今人又能品出几分滋味?
古人的茶,“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古人冲茶的泉:“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噀天为白;又如轻岚出岫,缭松迷石,淡淡欲散”;古人冲茶的器:“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气,余戏呼之‘兰雪’。”这样的饮茶,才是“人要诗意地活着。”
这样的“饮”,我只能遥想其萧朗风致。看中医,测我身为“痰湿型”体质,问方,答曰“常饮茶,以春茶为好,以绿茶为好”。我喜欢绿茶,连名字也那么好听,“碧螺春”,“野雀舌”或故乡的“谷雨尖”,都携带着明丽的春意。绿茶以最简单的玻璃杯冲泡,沸水浇灌,茶叶翻滚,隔杯凝视,一团绿载浮载沉,香气氤氲。那微苦顺喉而下,如小苏打冲刷积年的茶垢,有轻盈的洒脱感。
一杯春茶,可漾来一个静夜,可得一窗虚静。开门七件事的“茶”,一般在上午。两人对饮或独饮的茶,宜春日午后,宜浅夜。宜窗边,窗宜木格。窗外有树,或竹,间有鸟鸣,风过也好。
茶要热饮,所以茶斟七分。你浅饮,我与你续水,你喝到的都是热的。也不是不可倒满,倒满了,就显得笨拙粗糙。
端杯送客,虽主客都明白,却依然风雅蕴藉。
人走茶凉,一勾凉月如水。
但月依然会满,剩茶会被倒在花盆里。洗了新盏,换了新茶,沏了沸水,来了客人,新朋或故旧。窗外鸟鸣,叽叽喳喳。
不经意看去,哦,又是一年江南春。
>>我要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