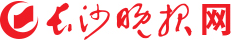散文 | 采茶
■蔡英
一场连绵的春雨过后,茶树的枝头嫩尖尖便舒展开来,长成一片浅浅的绿荫。清明前后,母亲提着竹篮去摘头道茶。头道茶色泽鲜亮,清香四溢,母亲是留给城里亲戚的。他们逢年过节带些旧衣服过来,够我们穿上数年。头道茶是他们最喜欢的,比梅菜、干笋、酸辣椒更受欢迎。
清晨,阳光暖暖地照在脸上,茶园里的野蔷薇、金樱子、金银花都开了,香气沁人心脾。找到了自家的茶树,我们低着头忙起来。一手抓住茶枝,一手快速摘下嫩芽。嫩芽儿绵软绵软的,有着饱满的汁液。茶园里热闹得很,大人们谈天说地,孩子们你追我赶,姑娘们婉转起歌。那些上下翻飞的手,宛若翩翩起舞的蝴蝶,采撷着茶叶的芬芳。
渐渐地,竹篮里的茶叶丰满起来,我们的手指也染成墨绿色。蹲在河边的石头上,将竹篮往水里轻轻一按,再慢慢搅动茶叶。如此反复清洗,再沥干水。晚饭后,母亲洗干净铁锅,嘱我生火炒茶。铁锅烧得快冒烟时,母亲将茶叶倒入锅内,持起锅铲使劲翻炒。鲜嫩的茶叶炒到绿油油软绵绵时,母亲便铲起来放到早就准备好的木盆里。她挽起袖子,蹲在地上,两手按住热气腾腾的茶叶,用力揉搓起来,直到揉出绿汁来。我端开铁锅,把竹制的茶罩放到灶上,有温热的火气跳到脸上。母亲便将揉好的茶叶,一把把均匀地铺在竹罩上。这时,她的神态极虔诚神圣,我隐隐觉得炕茶是件极重要的事情。
灶间的余火发出微弱的火光,母亲的脸忽明忽暗。她从柜里掏出些干黄藤,扭成一团,小心翼翼地堆在余火上。一会儿,黄藤燃烧起来,散发着浓郁的香味。每隔一段时间,母亲便持着煤油灯凑近看看,抓起一把闻闻,再翻动。如此,直到深更半夜,茶叶烘得差不多干了,她才放心睡去。次日清晨,房屋里便飘着浓烈的茶香,茶叶已熏成黑褐色。我喜欢把它们噙在口里,清苦中有淡淡的甜。走远路时,这样含着极解渴。
白露时节,茶不像春茶那样娇嫩不经泡,也不像夏茶那样干涩味苦,而有种独特的甘醇,我们往往被母亲差遣去采茶。新茶醇香,却易上火,我们不敢多喝。老叶子茶口感差些,伏天用老陶罐泡着,却很清甜。我在外地上大学常常要带上一大包茶叶。喝着喝着,思乡之情得以缓解。
十多年前,茶园被征收,而母亲似乎有先见之明,多年前便在屋前屋后栽了一批茶树,自家吃的绰绰有余。每年春暖花开时,母亲和老伙计们还相邀去山里采野茶。深山长年云雾缭绕,气候独特,老茶树汲取天地灵气,较山下的茶更为色泽鲜亮、清凉可口。母亲爬山越岭,奔波一整天,连夜熏好也不过一斤茶。
深夜,读书累了,泡上一壶家乡的茶叶。热气蒸腾间,茶叶一点点舒展开纤细的身子,深山的草木香扑面而来。闭上眼,一树树老茶郁郁葱葱,翠色可人,而母亲低着头佝着背采茶,一头花白的头发在风里飞扬,额上细密的汗珠摔落在茵茵的草地上……
>>我要举报